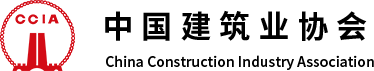作者:丁榮貴,系統工程專業工學博士。現任山東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山東大學項目管理研究所所長。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歐美同學會會員,中國建筑業協會工程項目管理專家委員。兼任中國項目管理研究會副秘書長、北京項目管理協會副會長、《項目管理評論》雜志編委會副主任、《項目管理技術》雜志編委、山東省干部教育培訓名師。
丁教授說:項目過程監管的關鍵是確保數據的客觀以及將其與管理者的個人特質和項目的組織特質相結合以形成有效的管理決策信息。
沒有對項目過程的管控,僅期待結果的驚喜是不可靠的。《扁鵲見蔡桓公》的故事說明了過程監管的重要性。扁鵲多次對蔡桓公說其有病,“不治將恐深”和“不治將益深”, 但蔡桓公沒有意識到這個重要性,反而認為“醫之好治不病以為功”并“不悅”,致使最后病入膏肓而死。
大數據時代,“數據”滿天飛,從其中辨識出真偽及關鍵的信息成為新的挑戰。無論是毛澤東的“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還是管子的“明于機數者,用兵之勢”,都是在談分析信息的重要性。
人們常說“要客觀地看待問題”,但在管理領域,客觀是相對的,主觀則是絕對的,所謂“客觀世界”無非是真正的客觀世界加上人的主觀解釋而形成的“主觀性客觀世界”罷了。換句話說,科學結論是不允許有反例的,其結論也不因人的解釋而變化。但是,管理的任何做法都與人有關,都會有反例存在,因此也會遭到有些人的不滿。管理并不能像科學一樣以真假來作為決策依據,而是以是否有效來作為決策依據的。
在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有很多有名的策士,他們靠游說各國君主而獲得利益和施展政治抱負,他們的言辭改變了很多國家,也產生了很多著名的篇章,如《鬼谷子》、《戰國策》和《說苑》等。佛教《金剛經》中有言“我相即是非相”,《無常經》中也說“世事無相,相由心生,可見之物,實為非物,可感之事,實為非事。物事皆空,實為心瘴,俗人之心,處處皆獄,惟有化世,堪為無我。我即為世,世即為我。命由己造,相由心生,世間萬物皆是化相,心不動,萬物皆不動,心不變,萬物皆不變”。《紅樓夢》中有一句“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還有無”的名言。這些都說明,事實本身(數據)不如人們內心對事實的想象和理解(信息)重要,或者說事實并不獨立存在,它只存在于人們對事實(數據)的解釋中。可能這就是管理學與自然科學的根本區別。
盡管對管理決策來說,數據不如信息來得重要,但數據的積累有助于產生信息,信息的價值也在于對數據的解析。數據到信息存在量變引起質變的辯證規律。毛澤東在其《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一文中說:“對情況和問題一定要注意到它們的數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數量的分析。任何質量都表現為一定的數量,沒有數量也就沒有質量。”在項目過程中,由于存在大量的變數,在過程中不斷收集數據以為決策提供有效的信息十分重要。但是,由于項目諸多利益相關方的利益立場不同、專業習慣不同和人員的流動性,保證數據的真實、全面、口徑一致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困難的,因此需要采取依據里程碑節點采集數據、根據標準格式匯總數據、根據實際與計劃的偏差度解析數據的工作方式。
如何做到數據的客觀以及如何將其與管理者的個人特質和項目的組織特質相結合以形成有效的管理決策信息,是項目過程監管中的主要矛盾。
要在項目過程監管中有效運用辯證邏輯,可以參考以下口訣:
驚喜常失望,可控在過程。
數據求客觀,信息求有效。
真假易分辨,判斷在人情。
清濁看魚種,掌管分大小。
一、“驚喜常失望,可控在過程” 的含義
管理者的字典中應該盡量摒棄“驚喜”二字,而以“可控”來取代它。追求“驚喜”的后果常常是“驚訝”或“驚愕”。從心理上講,信息的缺乏往往會導致人們往壞處想,對于那些人們特別看重的事情尤其如此。孩子放學比預期的時間晚到家,很少有父母認為孩子碰到好事了,絕大多數都是懷疑孩子身上是否發生了不好的事情,例如車禍、被老師留下、去網吧等。企業也同樣如此,當項目有一段時間的進展不透明時,人們往往會懷疑項目遇到了麻煩,要么是工期拖延,要么是經費出了問題等。項目的成功需要治理者、管理者和實施者等利益相關方各司其職。有人承擔責任不意味著他們能夠和應該承擔責任,不可控制就不可管理,僅靠事后的獎罰不是管理者應該采取的有效態度。將項目過程當成一個黑箱,實際上是將管理的責任放在那些很可能承擔不起這些責任的人身上。
二、“數據求客觀,信息求有效”的含義
在管理實踐中,沒有數據支持的決策常常會陷入因主觀臆斷而產生的陷阱之中,但是,數據若要反映客觀的項目狀況,就需要預先制定結構化的、標準的數據結構,要具備統一的測量方法和工具,沒有標準的統一就無法比較。按照辯證邏輯,“量變引起質變”的實現需要數量積攢到很大程度才會發生,而項目都是特殊的,如何才能保持足夠大的、具備統計規律的數據呢?這就需要在項目中按照里程碑采集數據,在企業內部按照項目集來進行數據采集。
數據變成信息的過程盡管是很具有創意的,但也有規律可循。“反常即是妖”,數據達到一定的統計規律后,那些與統計規律相差較大的樣本點就成了最有價值的決策信息來源,因為符合統計規律的工作即使沒有決策也會因為慣性而延續一段時間,但那些“突變點”如不得到及時的判斷和處置將會很快扭轉統計規律的走向。這種信息分析的思想是基于風險考量的。
項目決策者和管理人員更多的是需要關注規律以外的事情,而將規律之內的事情交給穩定的職能部門來處理。這就是辯證邏輯中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對立統一關系,也就是王宗岳在《太極拳論》里所說的“立如枰凖,活似車輪,偏沈則隨,雙重則滯”。沒有穩定的部門抓住穩定的規律,項目就容易缺乏可靠性;而沒有項目決策者和管理人員對異樣信息的靈活判斷,就不能使項目管理具有足夠的有效性。
三、“真假易分辨,判斷在人情”的含義
項目過程監管的一大挑戰是判斷利益相關方提供數據和信息的真偽性。但是,對管理者而言的真假與對自然科學家而言的真假頗為不同,前者常常基于人的判斷和接受度,而后者更傾向于與人的判斷無關。前者更像藝術,后者才是科學。《呂氏春秋》有一則寓言故事:“人有亡斧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斧也;顏色,竊斧也;言語,竊斧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斧也。俄而掘其谷而得其斧,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斧者。”管理決策基于決策者的判斷,而判斷會因決策者的閱歷、知識、情緒等不同而變化。
《鬼谷子》中提出“見其謀事,知其志意。事有不合者,有所未知也。合而不結者,陽親而陰疏。事有不合者,圣人不為謀也”,而諸葛亮提出“隆中對”也需要先問清楚劉備一個問題——“敢問將軍之志”。這些說的都是信息的價值并非基于冷冰冰的客觀數據,而是基于利益相關方的人情、心理和需求。《菜根譚》提到的“文章做到極處,無有他奇,只是恰好”也是說的這個道理。
四、“清濁看魚種,掌管分大小” 的含義
《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篇》中有一句中國人熟知的“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意思是說處理矛盾不要太理想化。中國人很講究面子,有很多項目監控策略只需要點到為止。管子說的“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說的也是這個意思。“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是中國人聰明所在,也是中國人的生存之道。監管者對被監管者需要有足夠的約束力,被監管者一般也認可監管者的權力,這是中國幾千年來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教育結果。
但是,過猶不及。監控者與被監控者只是角色的不同,并不意味著其智商的高下。當“君不君”時就會產生“臣不臣”,也即會產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對齊宣王所言的“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中國人講究投桃報李,講究“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在項目監管過程中, 需要根據項目的特點和利益相關方的特點,確定監控的松緊程度,對那些非原則性的問題要保持一定的彈性,給予管理人員足夠的靈活機變的權限,要學會“睜只眼閉只眼”,還要會“抓大放小”,這樣才能保證管理人員和普通項目團隊成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才能解決因項目特殊性而產生的一些難以通過規范化制度解決的問題。